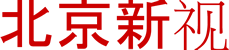华盛顿 — 现年97岁的法官保琳·纽曼(Judge Pauline Newman)是法庭上最年长的全职联邦法官,尽管人们对她是否能胜任工作表示担忧,但她的同事们仍在努力摆脱她。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一直与华盛顿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的法官们陷入法律纠纷,他们试图向她施加压力让她退下。纽曼进行了反击,仍在争辩一项禁止她审理案件的决定。纽曼是由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4年任命到这个负责处理复杂专利案件上诉的法院的。在拒绝参加作为司法伤残调查的一部分的神经测试后,纽曼受到了制裁。“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纽曼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说。“就好像我的整个一生,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致力于这项工作,现在变得毫无意义。”当民主党人在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辩论中表现糟糕后决定他已不适合担任总统候选人时,一个多方面的压力运动成功说服他退下。但是,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拥有终身任命,没有简单的程序可以让他们退出。随着人们普遍寿命更长,终身任命现在可能会持续数十年。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联邦法官的平均年龄为69岁,没有清晰的方式来迫使某人退下。“这是一种特色,而不是错误,”曾是纽曼的律师格雷格·多林(Greg Dolin)说。“没有办法摆脱法官,但我认为这不是需要修正的事情。这是需要庆祝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些法官并不希望继续终身任职,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失去理智,法院已经制定了措施来协助他们。“法官们从事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有责任向公众尽力确保在履行和执行那些可能产生非常广泛影响的职责时,我们在精神和身体方面都处于最佳状态,”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长期任职的联邦地方法官菲利斯·汉密尔顿(Judge Phyllis Hamilton)说。急需解决的问题法官们退休的压力通常只有在涉及最高法院大法官时才会公开。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任时,自由派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拒绝了自由派呼吁她退下的呼声。当时,她已经80多岁,并且曾多次患癌症。她于2020年9月去世,当时年龄为87岁,这使得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有机会用坚定的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取代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将法院转向目前的6-3保守派多数。尽管最高法院吸引了最多关注,“问题在更低法院可能更为严重,”法院监察机构“修复法院”(Fix the Court)执行主任加布·罗斯(Gabe Roth)说。根据美国联邦法院管理办公室的数据,截至去年,有870名活跃联邦法官,包括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13个上诉法院和94个地区法院的法官。根据联邦司法中心有关法官数据的NBC新闻分析,其中有70名地区法官和34名上诉法院法官有资格退休转为“资深法官”,资深法官承担较小的职责但保留头衔,或者全薪退休。不仅在总统竞选和司法机构中年龄增长是一个因素。据国会研究局的数据,众议院成员的平均年龄已经接近60岁,参议员平均年龄为64岁。去年,焦点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身上,她在任期内显示出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之后在年龄90岁时去世。这让一些人声称美国正朝着老年政治统治的方向迈进。“我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一些特殊之处,一旦他们享受了很多权力,他们担心如果放弃了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和被忽视 —— 你知道,他们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他们会变得边缘化,”耶鲁大学法律和历史教授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说,他最近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在司法领域,纽曼只是14名仍被列为全职审理案件的年龄大于拜登的法官之一,根据NBC新闻调查。巧合的是,三名最年长的活跃法官坐在同一家上诉法院上。除了纽曼,还有89岁的法官艾伦·劳里(Alan Lourie)和87岁的法官蒂莫西·戴克(Timothy Dyk)。在地方法院级别,纽约北区法官大卫·赫德(Judge David Hurd)今年已经87岁,是最年长的活跃法官,根据联邦司法中心的数据。他由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于1999年任命,并最近宣布计划退休转为资深法官。他之前曾撤回过退休承诺。第二年长的是出生于1938年的马萨诸塞州法官纳撒尼尔·高顿(Nathaniel Gorton),他是由共和党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 Bush)于1992年任命的。这些法官都拒绝接受采访请求。还有数百名年迈的法官仍在任职,但已经选择了资深法官的身份。司法机构对于有多少资深法官仍在积极工作并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一份2023年的司法业务报告表示,有520名资深法官被分配了工作人员,表明他们在进行至少一些司法工作。这些所谓的“活跃”法官是那些更受关注是否退休或拒绝退休的人,因为当他们宣布退休时,总统将有机会任命一个年轻得多的接替者。放弃活跃身份并不意味着放弃司法薪水。根据司法规则,任何法官都可以在65岁时退休或转为资深法官,这意味着只要他们在职满15年,他们仍然会得到报酬。事实上,转为资深法官可以是“最好的两全其美”,法律历史学家大卫·加罗(David Garrow)指出。“你可以选择做多少你想做或不想做的事情,”他说。纽曼多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她表示基于她丰富的经验,她仍然有很多可以提供的东西。她抱怨同事们在2023年初给她发出最后通牒时毫无努力以更友好的方式接近她。“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的同事们决定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采取这种处理方式,”纽曼说。她的事件描述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金伯利·摩尔(Kimberly Moore)的说法不同,摩尔负责对纽曼采取的纪律行动发挥了关键作用。摩尔在一份2023年3月的法院命令中写道,纽曼曾患有各种健康问题,有时导致她“无法履行活跃法官的职责”。摩尔写道,法院工作人员还对纽曼的行为提出了其他担忧。2023年初,与纽曼的说法相反,有几名法官直接向她表达了担忧,并敦促她考虑转为资深法官,摩尔写道。摩尔拒绝了采访请求,她说只有当这些努力失败时,她才会进行调查。“我与纽曼法官会面约45分钟,我概述了关于她无法执行活跃法官工作以及工作人员对她的精神状态担忧的问题。她拒绝考虑转为资深法官,称她是唯一关心专利体系和创新政策的人,”摩尔写道。纽曼的案件是一个例外,因为关于她是否应该退下的讨论已经如此公开,并导致牵涉到一个1980年的法律,称为司法行为和伤残法(Judicial Conduct and Disability Act)。该法律允许对被指控由于精神或身体残疾而无法履行职责的法官提起投诉。该法律允许对有资格退休的法官在经过漫长的程序后被取消活动服务资格,包括上诉。通常,关于法官是否应该退休或转为资深法官的微妙问题完全在幕后处理,其他法官温和地给予被质疑人士提供建议,甚至向家人寻求帮助。法院在司法系统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他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不需要更多的正式程序。在旧金山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管辖范围内任职的法官可以拨打一个专门为担忧同事的法官提供帮助的机密热线。担任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健康委员会主席的北加利福尼亚法官汉密尔顿自己在2021年退休转为资深法官,她负责监督各种帮助担心认知能力下降的法官的举措,包括培训课程。她说,法官们被鼓励提前做好计划。“我们认为每个法官都有责任确保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她补充说。政治也是指导法官何时退休的因素,因为许多法官会协调退休时间,以确保接替他们的总统是任命他们的总统的同一政党的总统。虽然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空缺时机一直受到关注,但自特朗普把它作为优先事项以来,对总统在选举下级法院法官方面的成功率进行审查已经增加。拜登也紹行了这一做法。在他的总统任期还剩下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任命了202名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同时强调多样性。特朗普在任内任命了228名法官。数据显示,104名有资格退休的活跃法官中有78名是共和党任命的,这引发了一些法官很可能正在等待另一位共和党总统的可能性。在法律界认识到当前系统的不足,这导致一些呼吁进行更具体的改革。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的律师詹妮弗·埃恩(Jennifer Ahearn)将这个过程描述为“相当随意”,并建议司法系统本身可能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司法机构自己认识到它需要做得更好,也许有一种更正式的系统,”她说。埃恩的团体支持拜登最近呼吁对最高法院实行任期限制的提议,有人说这一改革可能违反宪法,她指出这种改革也可以应用于整个司法体系。一些建议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包括一项提议要求70岁以上的法官接受认知测试。修复法院的罗斯还指出,通过立法增加法官人数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减轻一些地方法官的压力,这些地方法官的工作司法系统目前在一些案件负荷较重的地区依赖于他们的工作。一项双党法案最近在参议院通过,可能会在众议院获得类似的支持。“减轻压力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在最需要新法官的地区创造更多法官职位,”罗斯说。劳伦斯·赫利劳伦斯·赫利是NBC新闻的高级最高法院记者。埃莉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