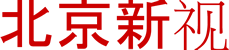黎巴嫩因以色列空袭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于周二被安置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学校建筑中。
在黎巴嫩首都中心的Ahliah学校的混凝土庭院周围,家庭们坐在塑料椅子上,分享着他们听说的在距以色列南部边境附近村庄被摧毁的房屋的消息。许多人于周二抵达,逃离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当局称这是几十年来公民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的数据,超过9万人在本周的两天内逃离家园,逃离强烈的以色列袭击,导致近600人死亡。以色列称这些袭击是针对真主党战士和设施的,这是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激烈交火近一年的加剧。
许多逃离南部的黎巴嫩人寻求在贝鲁特和其他地方的亲戚处避难,或者寻找要租的公寓。但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其中约4万人在200多所学校寻求庇护,黎巴嫩政府要求这些学校安置流离失所的人们。在世纪老Ahliah学校的金属大门外,周二有满载疲惫乘客的汽车停靠。一名援助官员示意他们前往其他作为临时庇护所的学校。24小时内有600多人抵达,没有空间了。原本应该是K-12私立学校的开学第一天。然而,Ahliah不得不清理桌子,把它们堆放在走廊上,为家庭腾出空间。一些教室的窗户上挂着儿童的衣物晾干。但大多数家庭来时身无分文,只有穿着的衣服。
一对夫妻坐在一旁浏览社交媒体视频,试图看看他们的家是否还在。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要求以长子阿里的父母身份被识别,使用Um Ali和Abu Ali这两个名字,分别意为阿里的母亲和父亲。Um Ali说,她被告知南部黎巴嫩一个村庄的18栋房屋被摧毁。他们12岁的女儿对空袭和他们逃离的经历如此震惊,以至于几乎没有说话。Um Ali说:“空袭就在我们的车边,孩子们尖叫哭泣。”她的丈夫手臂上裹着绷带,一个月前被以色列空袭的弹片击中,母亲把10个家庭成员塞进一辆车,周一开车南下。她说,当他们开车离开时,街上到处都是血。你会看到一个孩子躺在你面前流血,却无法做任何事情来帮助。
周一,有太多人逃离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士兵将分隔的高速公路变成了朝北的单一路线。通常一个小时的50英里车程,延长到了七八个小时,惊慌失措的家庭挤进他们能找到的任何车辆。Um Ali说,除了不说话,她的女儿还无法入睡,心跳加速。女孩站在母亲身后,说自己没事,但随后埋头哭泣。她的父亲说,战士在战争中受伤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孩子的影响是另一回事。她母亲说:“突然间,有人让你的孩子生活在恐惧、血腥和毁灭中。”父亲Abu Ali问:“美国人会接受这种情况吗?”流离失所后,失落感还没有出现。Abu Ali是一名建筑工人,他和妻子以现在时谈论他们在边境村庄的生活。他说:“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我妻子在家里,我的孩子在学校,我们在南部有一所带着新鲜空气的漂亮房子。”Um Ali补充说:“我种植一切,还养了几只羊。”她的脸上一瞬间闪现着对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我们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和东北贝卡地区瞄准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及其武器和火箭发射器。以色列还袭击了贝鲁特北部和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目标。这些袭击还导致数百名平民,包括数百名儿童死亡和受伤。真主党自去年10月开始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作战以来,一直受到空前袭击,其中包括上周数千个传呼机和对讲机的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亡,包括儿童,并导致3500多人受伤,据黎巴嫩卫生官员称。以色列被广泛认为是引爆这些设备的责任方,但以色列政府尚未确认任何参与。
在学校后面,几个男孩在一个混凝土足球场上踢着一只蓝球。在庭院里,来自边境小镇Nabitieh的两姐妹坐在一堵低墙上。年轻的那个18岁,最近修了一把鲜艳的紫色指甲。她姐姐20岁,长发精心梳理。年轻的姐姐努力描述经历空袭并匆忙逃离时的恐怖。她说:“太可怕了,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她补充说,他们在空袭开始时穿着衣服睡觉,以便第二天早上早早逃离。她姐姐说:“每天晚上飞机都会经过,吓唬我们。有声爆和非常近距离的袭击。”由于担心安全,两姐妹都不希望使用自己的姓名。在通往贝鲁特的漫长可怕的车程上,她们说,为了防止车辆被击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死前的穆斯林祈祷。当她们周一晚上抵达原计划逗留的南部郊区时,以色列飞机也在那里发动袭击,迫使她们在市中心寻求庇护。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大多数什叶派郊区Dahiya,瞄准真主党指挥官,但也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杀死平民。
首都的街道上挤满了流离失所的家庭。对于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来说,酒店也是如此。在一家酒店的接待处,一名男子要求五间房间,但只是为了一晚,直到家人弄清楚他们的选择。在另一家市中心的酒店外,咖啡桌上坐满了拿着零食袋的家庭。“我们一直在努力找公寓,但现在每个人都要求那么多钱,或者要求提前六个月的租金。”一名女子和她的姐姐坐在一张桌子前说。像大多数流离失所的人一样,他们不希望被识别,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这名女子是一名超市收银员,她离开得如此仓促,甚至没有携带身份证件。“导弹像雨一样落下,”她说。她和她的姐姐已经经历了三场与以色列的战争。但她坚称,这一次已经是最糟糕的了。珍·阿拉夫在贝鲁特报道,威廉·马克思在伦敦撰写。